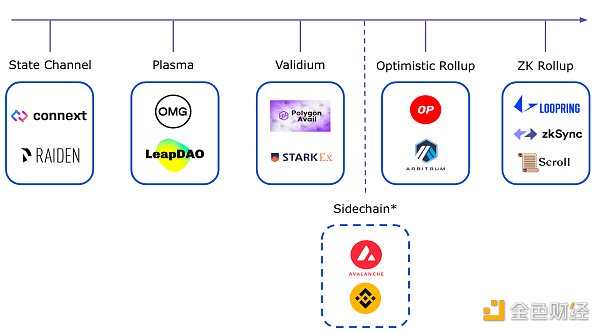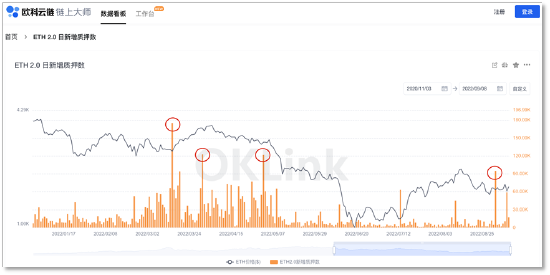风口背后:第一批00后Web3创业者,和他们的“人间清醒”

年轻人其实想得没那么复杂。
采访 | 苏子华、段宛辰
作者 | 苏子华编辑 | 靖宇
当不少 80 后、90 后还在困惑,生怕赶不上这趟所谓的 Web3“革命快车”的时候,有一些 00 后早已“玩得飞起”。一位 00 后朋友说,“你们眼中的革命,是我生活的日常。”
然而,这个新赛道有的不止是“狂热”,一些更年轻的先行者开始更加冷静,甚至反思。
我们和 4 位“玩”Web3 的 00 后创业者详细聊了聊,他们的故事和经验,或许能折射出行业的另一面。
01
入局,在青春期
福建人 Meepo 出生于 2000 年,“财务自由了”。
他定义“财务自由”的标准是,资产够买一线城市两套房加两辆车。这是他作为一名拥有十年经验的 Web3“老兵”的战绩。
Meepo 小学六年级时就接触了比特币,那是 2012 年,金融博士毕业的父母出于兴趣,正在尝试比特币挖矿。为了阻止 Meepo 继续沉迷游戏,便鼓励他“研究一下”比特币挖矿,每挖到一个币,奖励 100 元(当时一个比特币价值 12 美金)。
那时,从实用性上讲,刚诞生两年的比特币并没有什么社会价值。不过,一位挖过矿的 Web3 投资人回忆,对于比特币来说,2012 年却是个转折点。
这事儿,和诺基亚“走下神坛”有关。
过去,诺基亚曾当过一段时间手机界的“顶流”,在中国很受欢迎,但国外价格比国内便宜不少。为了防止在海外售卖的手机流入中国,诺基亚设置了“软件锁”,但有人破解了这个软件锁,可以将手机系统改成适配中国运营商的系统。很快,破解方法流入了中国的华强北。从此,用电脑破解从国外“走私”进入中国的诺基亚手机成为了一项华强北的特色业务。
但只用电脑破解还是有些慢。于是,有人发明了一个显卡加速程序,可以让显卡参与破解诺基亚的软件锁。这个“灰色”产业迅速爆发了,解锁一台手机的利润在 200-300 元之间,大量商户参与其中,形成了最早的一批显卡“矿工”。
然而,从 2012 年开始,随着诺基亚的没落和“矿工”的内卷,一台手机的解锁费已降至 10 元,甚至 5 元,没什么利润可赚了,一大批“矿工”面临失业。
就在这时,“救星”降临——比特币显卡挖矿程序诞生了。该投资人回忆,当时没有交易所,比特币通常在论坛和 QQ 群里交易。“我入坑的时候一天能挖十几个比特币。当时差不多是 50 元一个币。”
“华强北那帮人根本不知道比特币是什么,只看挖矿能不能赚钱。”这些靠“刷机”诺基亚为生的人迅速转向了用显卡挖比特币。于是,“中国在那个时候突然间冒出了一批非常专业的比特币挖矿算力,这可以算得上最早一批“矿工”的由来。”
远在广东的这批专业“矿工”的入场,间接地让 Meepo 的挖矿生涯提前结束了。普通笔记本的算力自然竞争不过专业的显卡矿机,Meepo 发现能挖出的币越来越少,一年后便放弃了,将挖出的少量比特币给了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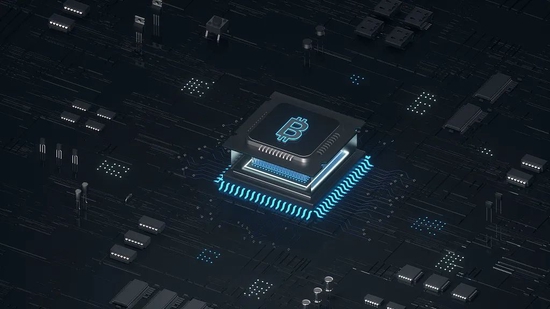
“那时没赚到什么钱”,但他对区块链的兴趣从此开始了。
和 Meepo 一样,2003 年出生的 Zohar 也早早接触了比特币。Zohar 对金融和经济学感兴趣,上高一的时候,从学校相关的社团里听说了比特币,又在网上自学完了浙江大学的博弈论基础课程。
再加上家里人都是做生意的,也在玩比特币,“我当时用 3000 元左右的资金买比特币随便玩玩,但后来基本都亏完了。”
Zohar 现在有多重标签:广东省某市选科高考状元、香港中文大学大一学生(已休学开启 Web3 创业)、某艺术 DAO 联合发起人、Web3 投资人等等。
他日常投资 NFT 的收益在数十倍左右。当他说出,年轻人不要被短时间内的财富收益冲昏了头脑时,作为一名资深“上班族”的我略微心情复杂。
Emma 开启区块链创业时年龄更小。她出生于 2006 年,今年只有 16 岁,在加州圣何塞的一所高中念书。Emma 在 11 岁的时候从父母那里听说了比特币,但兴趣不大。
这里是硅谷的中心,去年,由她创造的互联网项目入围了 YC 训练营(曾孵化出众多独角兽的美国著名创业孵化器)的前 10%。今年,她将这个 Web2 项目升级为了 Web3 项目,打算再次冲击 YC,希望获得投资。升级的理由很简单,项目愿景需要依托区块链技术来实现。
无论 Meepo,Zohar,还是 Emma,进入所谓的 Web3 都不是刻意为之。
就好像,一位在加密货币交易所上班的程序员,忽然发现,自己工作的领域在今天多了另一个称谓——Web3,自己好像也更值钱了。可即便参与其中也未必说得清楚 Web3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他,为什么觉得 Web3 是未来。
他想了半天,挤出一个答案:“年轻人喜欢的不就是未来吗?”
02
“这里没有权威”
无论在 Web3 创业还是在 Web2,对于 Emma 来说,只是一种学习的方式。“我学习的方式就是通过我的创业项目,每当我有问题的时候,我就去查阅资料或请教别人。”
Emma 说,不同于其他生活在美国的亚洲孩子那样重视考试成绩,她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热衷的事情上。“当我发现我对什么事情充满热情的时候,我就去追求它,跟随让我快乐的东西。”
Emma 的父亲 Kavin Zhang 毕业于清华大学,他告诉我“大多数家长把教育目标定位为一个比较肤浅的、容易显摆的、且十分一致的目标,比如上常青藤名校之类的。”但他从不要求 Emma 也上名校。
即便他深知名校光环带来的终身收益,但他更看重孩子的独立意志和自我约束,他总是问 Emma,你想做什么?
9 岁那年,Emma 开始写作,至今已经出版了 4 本现实题材的小说,正在写第 8 本书。为了把这份激情和热爱分享给别人,2020 年,她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线上组织,教别人写作。在这个组织中,她举办了写作比赛,也会邀请其他演讲者来分享写作经验。
Emma 发现,一个作家仅仅通过写书很难赚钱,很多作家不知道怎么推销他们的书。
为了解决作家的收入问题以及作品营销推广的问题,她创办了一个 Web2 的数字出版平台叫 Quillmates,又在今年重新把项目搭建在了区块链上,更名为 Cypher。靠着从亲戚朋友那里筹得的几万美元“天使投资”,她雇了人写代码,而自己则负责代码之外的产品原型、商业模型设计、运营等工作。
在 Cypher 上,用户可以发布文章,同时为读者提供“付费阅读+投资”的模式,允许读者投资作者。这样,作者可以发布自己的代币,当一个作者升值的时候,读者手中持有的代币便会升值,这样也给了读者支持作者、营销作者的动力。
“这将是一个自由市场,任何受读者欢迎的东西都会自动拥有更多的投资空间。”Emma 在向我介绍 Cypher 时是这样说的,“我想要的只有在 Web3 上才能实现。”
她观察到,在 Web2 的世界里,“像 Meta 和 google、YouTube、Instagram 和 Twitter 这样的社交媒体巨头,平台可以控制他们想要控制的任何内容,也可以审查他们想要审查的任何内容。”
而在 Web3 中,没有中央权威,所有人都是区块链的共同所有者。“让内容真正实现自由的唯一方法,就是在 Web3 上构建它。”她说。

很多人将 Web3 视为新世界的入口、希望改写曾经由老巨头们写下的“过时”的底层商业规则。这也更接近于当下“门外”的年轻人们试图进入 Web3 的理由。
比如,定慧对 DAO(去中心化自治组织)一见钟情,这种不同于传统公司的商业组织是 Web3 最让他兴奋的地方。今年做过一段时间某 NFT 项目运营合伙人的他,在一年前决定加入 Web3 的“圈子”时,还没有任何链上企业的实操经历。定慧是陕西人,出生于 2003 年,学只上到高中,其中有八年的时间是在家上学。
小学五年级时,身为大学教师的父亲为他办理了退学——理由是,眼见孩子在学校待了几年,“每天熬夜做作业”,“把身上的很多灵气都丢掉了”。从此,没再经历过体制内教育。
最初,家里人会帮他找一些课程、项目实习,用他的话说就是“在社会中与优秀的学长、前辈的共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比如,普通人该上高一的年纪,定慧参加了一个大学生社团联盟,成为了社团的志愿者,开始为社团的公众号打杂,从此进入了新媒体这行。此后,他一直在各类项目中实习或工作,直到现在将近三年时间。
早在 DAO 这个概念出现之前,定慧觉得自己就已经在“践行”DAO 了。大概是高二的时候,定慧做了一个凝聚了数百位在家学习、休学、退学少年的网络社群,“秉持着的理念就是人人平等、自治”。
后来,定慧给一位叫安猪的做教育创新的老师做学徒,学习了怎么做社群运营、写作、项目管理。“我觉得他那边团队的自治氛围,虽然没有智能合约,但也类似于 DAO。在各个城市,成员都可以组建那里的分部。他们在教育创新、社会创新、组织变革方面探索较多。”
入坑 Web3 是在 2021 年。定慧在北京实习期间,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聊区块链和 Web3。“所以当时遇见 DAO 后就很惊喜,因而入坑。”刚接触 Web3 时,定慧每天都泡在 DAO 里。在各式各样的微信群里,起初他看不懂聊天内容,但感觉自己“一直在学习”。因为在社群里的积极发言,他受到认可被邀请参与一个 DAO,并成为该 DAO 的运营,“他们给我开工资。”
某种程度上,在 Web3 领域里的年轻人中,反叛元素的出现频率极高。Zohar,这位高考状元喜欢称自己为“坏学生”,“喜欢做点不一样的事情”——高一时,Zohar 利用各类网课资源为自己制定了一份独立的学习计划。
“为什么不论老师还是学校,都希望大家按照一个相对标准的节奏和要求去学习或研究?我理解,毕竟管理这么多人,需要一个比较统一的、适合大多数人的方式来提高效率。”Zohar 说,“但我并不认为我属于大多数人。”
此前他的成绩属于中游,几乎不怎么听讲,通过在网上自学,他习得了大量的知识和有关高考的经验,后来高考时,一跃成为全市的高考状元。
仅仅半年后,他再次做出不同寻常的选择。在完成大一上半学期的课程后,Zohar 便从香港中文大学休学,投身 Web3 创业:发起艺术相关的 DAO,参与策划欧洲首个高规格加密艺术展;后来还成立了加密货币基金,成了一名投资人。
Zohar 觉得,在现有的环境下,普通人想实现自身价值、获得可观的收益,甚至跨越阶层是有难度的,但“Web3 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和希望,在这场浪潮中,每个人的影响力都可以被放大。”——这主要体现在财富转移的速度足够快。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在一场交流会上,关于区块链的财富自由的传说随处流传,让他们相信,每一个人在参与 Web3 的过程中,都有可能获得超额的财富。
年轻人们渴望颠覆权威,甚至成为所谓的“权威”。但成为那个幸运儿的几率究竟有多大呢?
03
“割”与“被割”
Zohar 在和项目方电话或者在线交流时,如果他不说,没人知道他只有 18 岁。“这就是 Web3 的匿名性”。
这点他说的没错。
我们的采访都是通过电话进行的,我并不知道对方是什么造型,长什么样。事实上,我也不方便做一次采访就让对方把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工商注册证明统统发给我,来验证他说的是否真实。
我试图通过他们的周边人来交叉验证真实性。但也不能完全保证。比如我没有办法完全验证——他们自称最多每周要聊接近 20 个创业项目;有人大学期间做了 20 多份证券、大厂、交易所相关的实习;又或者,投资加密货币的真实回报率。如果对方想忽悠我的话,想必还是比较容易。
这是 Web3 创业圈中的常态。一位在币安(目前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工作的朋友曾提醒我,“不要完全相信币圈人说的话,将他们说的财富先去掉一个零,再打个对折。”
“这个圈子有财富神话,但凤毛麟角。”Meepo 说。
2014 年接触以太坊网络后,Meepo 参与其中,认识了很多项目方,“早期很多人后来成为了圈内大佬。”后来,他带头组建了社群,逐渐壮大。通过为一些项目方转发项目到群里做宣传,Meepo 获得了一些“内幕信息”,比如某个时间点将会有大量资金进来,他就去做套利,“差不多是从 18 年开始,慢慢的就财富自由了。”

“社群里的人不少也因此赚到了钱,大家逐渐信任我,成了我的粉丝。”
当 Meepo 承认自己某种程度上也属于是靠“割韭菜”实现了财富自由时,我惊讶于他的坦诚。
“币圈怎么赚钱?就是靠消息不透明性赚钱。”他见到国内一些 VC,早期通过 all in 的方式实现了一夜暴富,之后便很快退出 Web3,去投资其他领域了。“很多 Web 3 项目方所说的什么基于信仰、基于共识去做一些事情,这些都是假的,当他们每个人都赚够钱了以后,就不会再有人谈什么共识了。”
电话中的我们沉默了一会儿。Meepo 接着说,“虽然我不喜欢这种方式,但我觉得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如果说要普度众生的话,我首先需要去实现自己的一些追求和目标。”
会有负罪感吗?
“因为我看不到谁在亏钱。区块链就有这样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知道现在是割谁的韭菜,所以就不会有负罪感。”但 Meepo 并不会允许在自己的项目里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定慧曾担任过一个宗教文化类 NFT 项目的运营负责人,接触了一段时间后,他揣测,投资方是“币圈的人”,可能想捞一把就走。
“一款头像类 NFT 最大的价值应该是使用者的人脉圈与牛市中的造富效应。但对于土狗 NFT 而言,通过一些叙事、营销手段为项目“赋能”,看似做的风生水起,其实只是虚假繁荣,没有真的创造价值。”
定慧最初选择加入这个项目,“一方面是的确有很多关于宗教的思考希望表达,更重要的是有机会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去运作,面对更大的挑战、收获一手的经验。”
“以我的背景,优质的项目方不会给我这个机会,但如果我有做过一次的经验,后续求职时就会完全不同”。在他看来:躬身入局永远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我现在已经退出了。”定慧明确表示,想要的经验已经拿到,“只是不愿再和这样不成熟的项目方合作了。这个项目可能没有什么价值,但我在做宣传的时候没有去故意欺骗或煽动大家的欲望产生购买,因此问心无愧。”
“NFT 目前本质上还是一个靠声量贡献的领域。”Zohar 说。他观察到,一个项目的优劣和它能否赚钱是两码事。一些项目“很稀有”、“有创意”,但团队对于用户预期的管理不行,导致项目不被市场认可,NFT 的价格一直起不来。“我们管这叫市值管理能力,通俗一点讲的话,有点像讲故事的能力。”描述得更直接些:你能不能让用户觉得买了你的 NFT 后能升值。
一位资深 NFT 买家向我们直言道,“大部分 NFT 项目都是割韭菜”。比如一个团队在开发一个 NFT 项目的初期,会描绘未来的图景(NFT 将如何升值)。而一旦发布了项目,用户买单后,就不再给这项目“赋能”(比如搞一些社区活动,邀请一些大佬来社区做分享),用户相当于只买到了一张图片。项目方基本是“空手套白狼”。
不过,Meepo 觉得自己有办法改变这种现象。他策划了一个主打 IP 二创概念的 NFT,并很有信心它会被市场欢迎。
“现在的 NFT 市场是一个炒作市场,很多人手上的 NFT 是卖不出去的,因为持有方是被动的。”他决定做一个能由玩家自己决定价格的 NFT——他为自己的 NFT 项目写了一篇 10 万字的玄幻开放式小说,用户买完一个 NFT 后,会获得小说里面特定的某个章节,可以对这段话进行创作。
“这样就能实现 NFT 的价值不决定于市场,不决定于项目方,而是持有者本身”他称这种模式为 create to earn,持有者可以通过二次创作来提高 NFT 的价值,“如果你想让自己的 NFT 卖一个好的价钱,那么你就要去通过二创的形式不断地修改,来达到买方满意的程度,卖个更高的价钱。”
“我不担心我卖不出去,我有我自己的后路。”他透露自己“手上有 3 个加起来人数近万人的社群”,“群主就是我”。这是他过去这些年“积攒下的人脉”。他相信,只要在这些社群里宣发自己的项目,“肯定有人买。”他称之为“圈层化的营销”。
但因为加密市场正处于熊市期间,Meepo 搁置了项目的发布,等待下一波牛市的来临。现在,他有另外一件同样要紧的事情去做。
04
下一站
“其实我对这个行业蛮失望的,Web3 应该倾向于技术,而不是金融属性或者炒作的东西。我对 Web3 又爱又恨。”Meepo 说,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助 Web3——今年从学校本科毕业之后,转身加入了某互联网大厂。他青睐互联网大厂 AI、元宇宙等方面的技术底蕴,“毕竟区块链只是 Web3 的一部分。”
“未来时机合适的话,我还是会回到 Web3 的。去中心化的的商业文化更吸引我,那会是未来。”
所谓的去中心化与当下的商业文化间差异的一种体现是,过去十几年,互联网行业的畅销书是《无限战争》之类看上去就剑拔弩张的成功学书籍,而 Web3 领域的流行书籍是《主权个人》,基调从争斗变成了平权、和平共赢。这背后,生意的底层逻辑在改变:强调社区而不是公司,强调个人而不是公司,强调成员而不是用户。
只不过,这种“去中心化”的未来依旧很远。今年 7 月份,定慧和上一份 DAO 运营、以及 NFT 项目的运营合伙人的身份,告别了。他写了一篇文章:《国人 DAO 大败局:放心吧!我们都实现不了去中心化自治》,复盘了当下 DAO 存在的问题。
定慧提出,当下很多基于微信开展治理的 DAO,和社群没什么区别;核心团队集权统治;开会繁琐,难以达成共识,没人做事;也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借着 DAO 的名义招摇过市,“实际上啥也不是。”
“人们常提到 Web3 信仰,我觉得是一种投射,是将人类的理想投射到这样一片新鲜的热土上。”定慧反思了 DAO,“它能不能变成现实?其实我不抱太大希望。”但他依旧在探索更好的 DAO 的实现方式。
8 月末,在 706 大理主办的“瓦猫之夏”Web3 大会上,定慧担任了 DAO 主题营地的主理人,这位 19 岁的朋友为从全国各地的“哥哥姐姐”们,策划、组织了 3 天的分享、共创活动。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Web3 当然不是终点,更像是人生的一段旅途、新的尝试或者说低成本的冒险。
Zohar 说,他终归有一天还是要回归校园,做更加深度的学习,开启下一项研究。“我在校外的经历和校内去研究的东西将会是互补的。我很渴求这方面的进步。”
他希望在回到学校之前,积累更多关于市场、明面上看不到的认知,和别人做大量的交流,去获得独家的见解与认知。去积累与人打交道、与项目打交道,以及关于投资的逻辑和经验。“当我觉得,我已经搭建完了一个相对完善的框架的时候,我会回到学校研究另一个体系的框架。人不能总局限于一个方向、事情上去努力,那样子可能不会走得非常远。”
年轻人的发迹故事就像爽文。他们作为社会资源最少的一个群体,底色其实是“Underdog”(在中国,理解为“屌丝”也行),如果连资源最薄弱的人都成功了,那理论上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人人都喜欢看年轻人的故事,也都希望自己能过得更好。
故事还在继续。
作为第一批 00 后 Web3 创业者,Meepo 加入了互联网大厂,Zohar 未来要回到学校,Emma 利用课余时间继续冲击 YC 训练营,定慧还在寻找 DAO 的机会:他们都有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