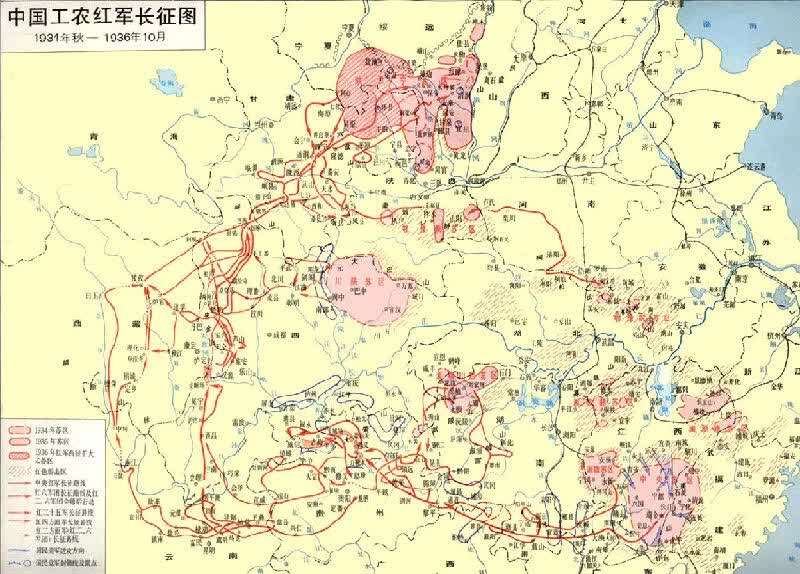上海人的讲究
不厌其详,一丝不苟,凡事讲究,是深入到上海人骨子里的一个行为准则。

上大学时,读到现代文学翻译家曹靖华先生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忆当年 穿着细事切莫等闲看》。言及他当年在上海求学时,曾到鲁迅处拜访。看门人见他那身打扮,一摆手“从后门走!”曹先生说自己“宛如一枚土豆,落入十里洋场”。还写到在上海无论白天生活的怎样,到了晚上一条裤子是一定要折得整整齐齐压在枕头底下,压出裤缝来的。在以衣帽取人的旧上海,穿戴时髦光鲜,出门往往会被高看一眼。
这篇文章让我对上海人的讲究有了最初的印象。
在上海呆久了,对上海人家生活的讲究有了更深一层的感受。一天和一位阿姨聊天,得知她家原是当地农户,后来城市扩建了,地被征收。她说,晚上回去要烧三样小菜,外加一汤。菜是一大荤,一小荤,一个蔬菜。汤必须要有的——“老头要吃酒”,天天都是这样。她笑着对我说。
大荤、小荤,这是我到上海后才获得的新知。大荤指的是用纯鸡鸭鱼肉或者海鲜之类做的菜,譬如红烧肉、红烧大排、红烧鱼、白斩鸡等等;小荤则指肉配菜模式,如肉丝茭白、青椒肉丝等等。一顿饭,光有这些还不行,纯蔬菜一只是必有的。所谓清清爽爽,荤素搭配,这顿饭菜才吃得爽,“有劲”。

因此,上海人家每天一大早,顶顶重要的一件事,是到菜场采购全家一天的“小菜”。说是“小菜”,其实包括了大荤、小荤或肉或鱼或虾或蟹的各种食材。所以,上海早晨最“闹猛”、最生气勃勃、最接地气的地方一定是菜场,无论春秋冬夏,晴天雨天,这儿永远人声鼎沸。无论荤素,讲究的是一个“鲜”字,要当天吃当天买,隔夜的打蔫的菜,是没有市场的。
记得有一年春节晚会,有个小品节目中一位演员扮演上海人,操着上海口音,嘴里左一个“小菜”右一个“小菜”,一副滑稽相,引起观众阵阵哄笑。笑声里有对上海人、对口口声声“小菜”的一种揶揄,以为“小菜”就是“小气”“寒酸”之意。现在我明白,这是对“小菜”这个概念,对上海人生活方式的一种误读。“小菜”是与酒店餐馆的“大餐”相对而言的,是指居家生活的家常菜,绝非是几根小葱、一把青菜的“便宜的菜”。上海人家的小菜,样式多,味道好,质量高。讲究时令、时鲜、稀罕、口味和营养。若是来了客人或没来得及买菜,也有补救办法:到熟食店去买“熟小菜”:什么酱鸭、烧鹅、叉烧、爆鱼、鸭胗、酱牛肉、油爆虾、狮子头……真正是让人眼花缭乱。就连南京路、淮海路这样高端时尚的地段,走不了几步,也会不断有熟食店出现。

其实,你要是有机会来上海人家里吃饭,你会惊异于他们对于生活,对于吃饭,对于每一餐“小菜”的认真、郑重。我的婆婆是道地宁波人,当年烧出的菜我觉得样样好吃无比。可是婆婆却说,姨妈(丈夫称为姨奶奶)烧的那才地道。可也是,姨奶奶比起我的婆婆来,烧菜更加讲究。上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在姨奶奶家吃到“海苔花生”“草头圈子”,才知道,简单的油炸花生米,搭配上翠香碧绿又有点海鲜味道的海苔,是怎样一种说不出的美味。后来在饭店里多次吃过,却怎么也无法与姨奶奶做的这道菜媲美。“草头圈子”呢,油油的猪大肠与淡淡清香的草头搭在一起,真是美妙的组合!还有黄豆猪脚汤、百叶包、蛋饺、虎皮鸡蛋……上海人讲究食材之间的搭配。百叶包,是用比较薄的豆腐皮包上肉馅。豆腐本来就有种特殊的香味,加上肉料的香,真是好吃营养而又不腻。像这样的做法,在北方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我还跟婆婆学过做蛋饺。先把鸡蛋打成蛋液,然后用一只直径约六七厘米的铁勺,在勺子里倒进蛋液,放到煤球炉火上(当然火不能大),左手把勺子轻轻转一圈,蛋液就会薄薄的在勺子里形成一张蛋皮。接着,再把事先调制好的肉馅放进蛋皮的一边,轻轻将另一边折压过去把馅包住,一只蛋饺就做成了。做汤的时候放上几只,鲜嫩黄色的蛋饺浮在汤面上,又激食欲又提味。虎皮鸡蛋第一次吃,是在复旦大学的教师食堂。为什么叫“虎皮鸡蛋”?原来是把煮熟的鸡蛋先在油里炸过,再加上若干调料后烧煮,鸡蛋表皮起了一层褐色的皱,叫法形象,吃起来更香。把一只普普通通的鸡蛋做成这样,颠覆了我的认识。
其实,不厌其详,一丝不苟,追求把事情做好,做得精致,即使在做饭这样的小事上也不敷衍不苟且,是上海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联想到我在上海的所见所闻,点点滴滴,感觉到,凡事讲究,是深入到他们骨子里的一个行为准则。(张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