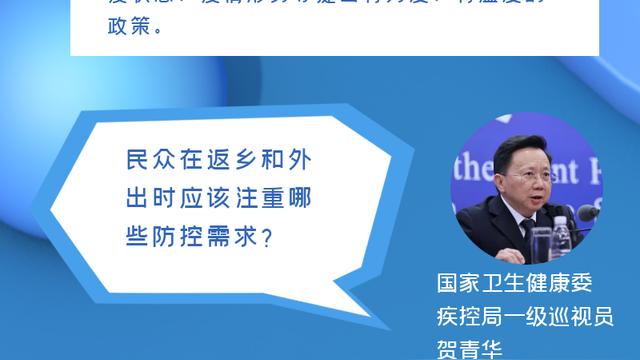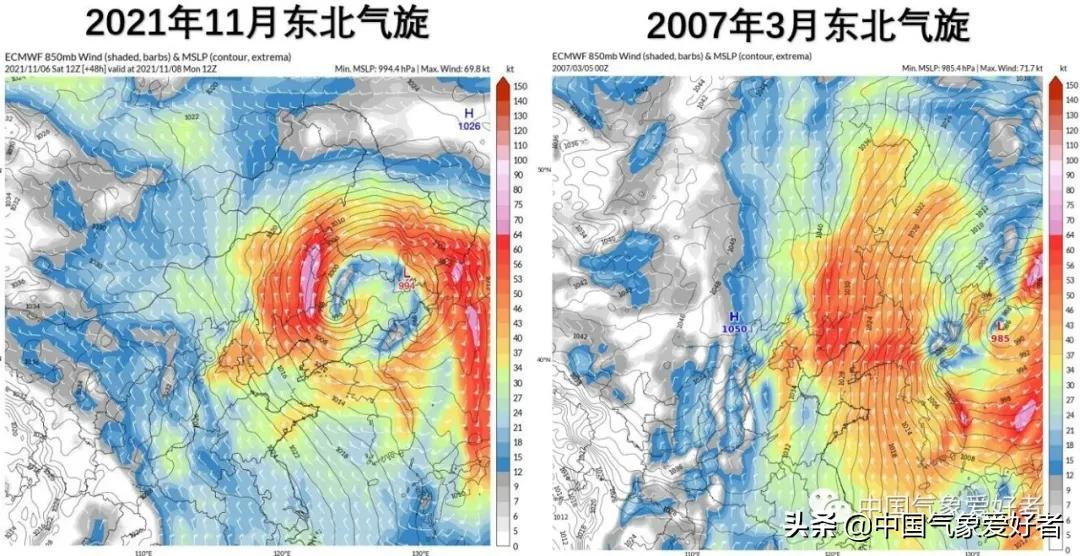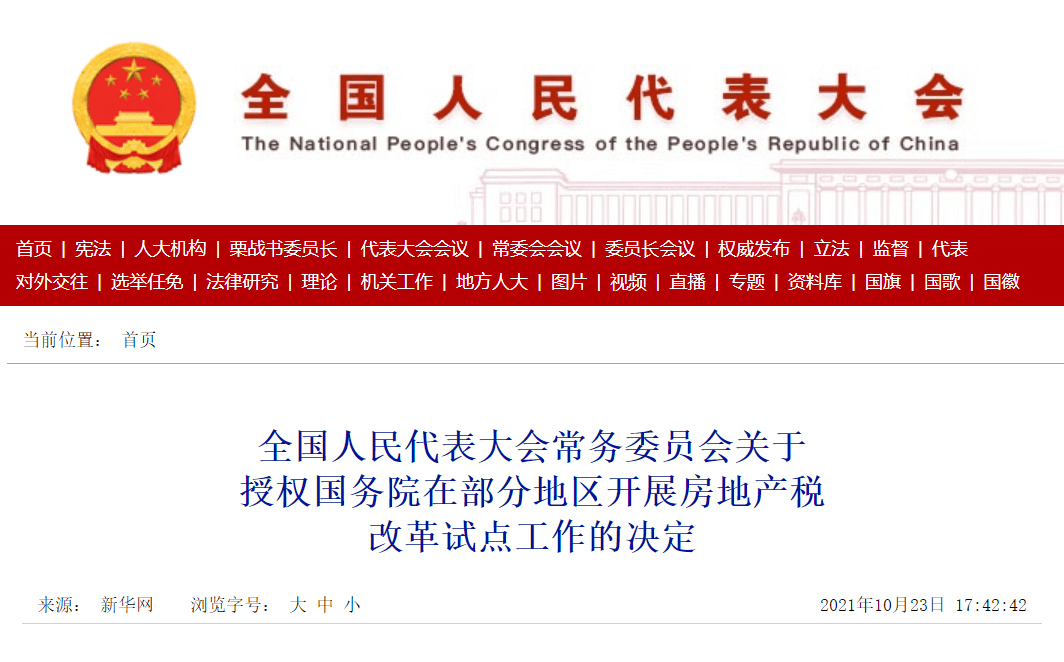《走进生命的花园》

编者按:本文的作者是一位人类学者。近九年前女儿还在妈妈肚子中逐渐成型时,出于即将为人父的兴奋、以及正在成为职业人类学者的自得,他一时兴起为她写了前面的几篇小短文,但后来很快就放弃了。
究其原因,他说,一方面是尽管身边有不少过来人的安慰和开导,但是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所谓羊水过多、胎位不正,很是让人高度焦虑;另一方面职业人类学者生涯的开端很不顺利,于是再也没有舞文弄墨、喜怒笑骂的逸兴了。没想到,这一停就是九年。
“九年换了人间,孩子们已经活生生地站在面前把我们气死半条命了。尤其此刻,两个孩子和我们朝夕相处了小半年之后,新发地疫情突然再次爆发,我们几乎完全看不到‘与君绝’的希望了。”
应橡果公号之约,在重新开始反思养儿育女之道前,这位人类学者父亲翻出旧日文章,且容我们从头说起。
1 人类学者如何传宗接代?
人类学这个学科有耳闻的人或许不少,真正了解的未必多。简单粗暴地说,人类学就是以沉浸式(参与观察)、移情式(主位观点)、映照式(跨文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他者的文化和社会,涉及到政治、经济、宗教和亲属制度等方面,最后达到理解自身的目的。尤其是亲属制度,可能是人类最早、也是最基本的社会文化组织形式,人类学家相信,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成熟理性的政治、经济、宗教制度,多半是从亲属关系慢慢演变而来的,并且直到今天也仍然无法摆脱亲属观念的深刻影响。
有点扯远了。我的意图是想说,正如人类社会的其他制度无法挣脱亲属结构的羁绊一样,号称洞察社会与文化原理的人类学家自身,在实际生活中也深陷传宗接代的泥潭之中,无法提供或实践任何超越性的解决方案。我本人就是一个活生生例子。
我和老婆都是人类学博士,虽然研究方向各异,但是基本训练是相似的,照理说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应该一致或接近一致才对,但事实是,我们在几乎每个重大选项上都南辕北辙。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究竟要不要秉承“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古训?
生不生?

《哈姆雷特》
这是个“To be or not to be?”式的本体论问题。我在东南沿海乡村长大,自小见惯了各种拜拜仪式,深知逢年过节时没有子孙来烧香磕头的灵魂该是多么惨淡潦倒。海外人类学家就指出,在中国人的分类世界里,有人祭祀的灵魂成了祖先,有许多人共同祭祀的就成了神,没有后人的就是野鬼。与此相反,我老婆生长在西南一个四方杂处的城市里,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军政人员曾经迁来该地,奠定了那里的“新文化”特色:今天街市上引车卖浆者所说的斤,实际上指的是公斤,这个差异当初着实震撼了我。科学、民主鼎盛之后自然也就不重神、鬼、祖先了,于是“生不生”这个问题一度就成了我们争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一方认为亲属关系再生产是人的天职,另一方则认为现实世界如此残酷,强加给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家伙简直于心何忍。争论既无结果,于是我们决定交给命运来裁决。所谓命运观,就是科学理性和鬼神迷信两者对它都不排斥的一种认识方法。非洲阿赞德人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当然都明白粮仓倒塌是因为白蚁蛀蚀了顶梁柱,可为什么被砸中的偏偏就是我呢?”白蚁是科学解释,但科学解释不了我被砸中的原因,就像科学也无法解释张爱玲之问:“噢,你也在这里吗?(背景是: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我老婆既然承认婚姻是一场无厘头的命运安排,那么传宗接代的事为什么不可以如法炮制呢?听天命的结果就是,我老婆怀上了。
生几个?

《小象的大家庭》
只要计划生育政策一天不改变,生几个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但这仍然不能阻止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争执。我老婆的思想一旦翻了身,忘本得比谁都快。她坚决主张必须要两个或以上,这样孩子才不会孤单。于是她设想像那些名人、高干、富豪一样在美国生一个、香港生一个,或者偷偷去我们熟悉的少数民族地区上一个藏族、彝族或蒙古族户口。对于这个问题的虚幻想象给她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因为我们的儿子或女儿显然有机会成为总统、特首、或活佛,并且不再需要为小升初、初升高之类的问题煞费苦心,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必凄凄惨惨戚戚地苦等北京房价降到“一潘”。我却认为“生不生”本身是个道德命题,“生几个”就变成了劳动异化和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因此坚决反对上述假设。这个问题本不需要答案,或者说答案早就在那儿了,因此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就像对散户什么时候翻身、楼市什么时候拐点的追问一样,我们实际上早已心知肚明。
叫他(她)啥?
这是上一个问题的延续。一方面,我老婆的美好设想是,如果生两个,第一个屈服于万恶的旧传统,随他爹去吧,第二个则必须彰显女性主义的崛起或复兴,随母姓,这样各适其所。正如上述,既然生两个是一个伪命题,于是我乐得送个顺水人情,提议第一个命名为“郑儿八经”,第二个称其为“伍所谓”。哪知这个提议捅了大篓子,她愤怒地指责我厚此薄彼,对父系的继承人青眼有加,对母系的后裔则薄情寡义。我只好再次诉诸南方农村的乡土知识和辩证法,告诉她名字取得贱反而容易生养,这才使得情感灾民的情绪稳定下来。另一方面,直面现实的话我们只能有一个孩子,取名字成了一个以父母双方的学识和趣味共同为其背书的技术活。孩子的名字后面,并不像学术论文一样,有第一作者、通讯作者的责权利之分,一旦孩子的名字贻人笑柄,谁来承担这个主要责任呢?反过来说,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孩子的名字如果就像iphone之于普通手机那样木秀于林,显然就能从起跑线一直赢到终点。这些可以预见的严重后果使得我们争锋相对的频率和激烈程度都明显上升,各自提出的方案包括汉字、字母、数字、图案及其组合,也参考了摩尔根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发现的神圣命名法则,甚至试图像赠送给台湾的大熊猫一样向公众征集名字。这个争论仍在进行,也许到报户口的那一刻才可以尘埃落定。
我相信,许多初婚初孕的年轻父母都争论过着上述问题或这些问题的变种,我也相信,势必还有更多匪夷所思的难题等着我们去面对。让我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是,尽管我们这般大相径庭,但在一个问题上,我们的步调如此一致,那就是:我们会共同晋升为父母,分秒不差,毫厘不爽。
(2011年秋于北四环博士后公寓)
2 在哪里生?
按照医学的算法,我们的不知性别的孩子已经50天了,但实际上,他/她的确切孕育时间可能要晚个二到三周;另一方面,中国人“十月怀胎”的传统说法,与西医40周的孕期也误差颇大。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不管“科学的”或“传统的”说法实际上都是一种自我约定俗成的文化表征系统,与现实不一定严丝合缝。换句话说,还在我老婆肚子里隐蔽然而坚定地膨胀着的这一团小肉球,已经被笼罩在各种文化规范的天罗地网中了。这些文化规范内部的抵牾常常叫人啼笑皆非。
怀孕之后的头等大事是找到愿意迎接他/她来到这个世上的医院。

我们都知道,耶稣诞生于马槽,佛祖在无忧树下降临尘世,藏族妇女往往独自(或者有一位年长妇女陪伴)在猪牛圈里诞下自己的孩子,这些事例说明人类对于婴儿出生地点的选择是有讲究的,也是不断变化的。但归结起来,其共通的一点是,新生儿都是在非人类(non-human)的环境中呱呱落地的,环顾四周是动物或植物,也就是人类居住其中的自然界。大概从现代科学制度兴起以后,在医院分娩渐渐成为了一种霸权式的文明标志。在医院里分娩或许是现代社会“脱魅”的指标之一,在婴儿睁开眼睛的那一刻,他/她首先看到了冰凉的医疗器械(科学),忙碌的白大褂、有些甚至是男大夫和男护士(专家),在一些新潮私立医院里,夹杂其中的甚至还有自己的父亲(性禁忌脱敏)。与此相反,在传统社会中,男性亲属是现场最需要避忌的人,他们只能候在屋外,等着接生婆高声报喜。换句话说,在我们最初的观念和实践中,母婴与其他人的第一次遭遇,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文化中介程序才得以实现,而现在这一切都以最简化直接的方式在医院里发生了。正如福柯指出的,医院是对社会空间和人类身体进行现代性规训的场所。
既然我们都已经是现代社会中的人了,于是医院成了我们唯一可靠的选择。但是且慢。
众所周知,医院的功能是对付疾病和死亡。尽管我们都承认生育也会带来不测后果,但就其总体趋向而言“生”还是作为“死”的对立面存在的,是人类延续并繁荣兴旺的唯一手段。因此,把产房放进医院这个大容器里,实际上带来了一个极其吊诡的客观后果,那就是降低了生育本身的文化形象。也就是说,怀孕的父母从寻找医院的那一刻起,就把自身置于病人的位置上了;我们梦寐以求的新希望——胎儿——居然成了我们身上一处可憎的疾病;我们急切地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是为了和我们身上的病灶分离。
医院因此在生育过程中奠定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再加上北京人口膨胀,医院设施严重滞后于形势的发展,相信北京的普通父母们都遭遇过求告无门的凄凉境地。既然疾病成了生育的隐喻,寻访名医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在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下,我老婆抱定非三甲医院不去的决心。我根据网上搜索得到的结果,挨家打电话过去询问,每一家妇产科的接线员都以店大欺客的口吻告诉我,本店客满,客官另寻他处吧。我又转向那些不那么出名的医院求助,结果同样并不乐观,只有极少数表示我们可以早点过来排队,至于能否成功则只有天晓得。
我的朋友们对我的天真举动简直捶胸顿足。他们说,申请产科病房和北漂子女入读北京公办学校之类的事,通过正当渠道来获得有效信息的可能性简直就和国足赢球、国乒输球一样渺茫。我试着联系一些朋友,我遥在南方乡下的父母也开始重新挖掘他们的社会关系,事情开始有了些许眉目,其中最叫人惊异的一条线索居然指向了某家医院的妇产科。如果说这家医院是中国医学界的皇冠的话,他们的妇产科就是皇冠上的明珠。我心跳加速的拨通了一位大夫的电话,注意,此刻的我不但掌握了她的私人号码,我还了解她和她父亲姓甚名谁——我将亲热地把她们叫做“小兰”和“我刘叔叔”,我还将毫不经意地提起,我的母亲给她打过一两件小毛衣。
小兰医生非常客气地摧毁了我的热切盼望。她表示在我老婆预产期前后的几个月内,都已经全部预约完毕;如果想寻求特批的话,必须经过某位主管院长同意,但她作为普通大夫实在无能为力。看吧,正如我的朋友们告诉我的,咱们这个社会的事情总是有活动空间的,他们管这叫“机动名额”,但不幸的是,我们的触角刚好够着了小兰大夫,却伸不到最后签字的人那里。这几乎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常态,就好像我们使用的这个网络,据说主干网的速度早已国际领先了,但是“最后一公里”却扼住了命运的咽喉。我仍然试图做最后的挣扎,小心翼翼地问询道:我们平时就不来麻烦你们了,但是最后分娩的时候可不可以来你们医院呢?小兰大夫再次惋惜地说:全北京都是相同的规定,你在哪一家医院建档、产检,你就必须在那一家医院分娩。没有哪一家医院接受别人的病人,没有!
我明白了。至少在一般状况下,至少在咱们这个国家,各家医院的产检病历还不能真正通用,现代医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所谓的标准化、客观化和可公度性。我们的医生对于某一位病人(产妇)的诊断和治疗,是建立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基础上的。人类家埃文斯-普里查德描述过一个完全相似的原始社会:非洲阿赞德人的巫术之所以能够治病,最根本的原因是巫师了解病人的全部社会生活细节。就当下的生育实践而言,现代科学体系似乎还没有真正实现范式突破,因为我们仍然在实践着阿赞德人的那一套。
当代人的生活世界里充满了文化批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2011年秋于北四环博士后公寓)
未完待续!
《少年》正式上线啦!